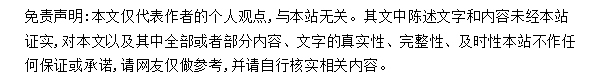自2015年底供給側改革開啟,已經過了2年半時間。近期,經濟參考報報道稱,今年去產能進入啃硬骨頭階段,去產能正式打響了攻堅戰。事實上,
自2015年底供給側改革開啟,已經過了2年半時間。近期,經濟參考報報道稱,今年去產能進入“啃硬骨頭”階段,去產能正式打響了攻堅戰。
事實上,去產能自2006年便開始了,只是供給側改革后的去產能更加具有系統性和強制性。時至今日,去產能究竟進行到什么程度?哪些行業依然產能過剩?弄明白這些問題,對于判斷中國經濟是否迎來新一輪周期有很大參考意義。
去產能的重點領域
我國的產能過剩問題自2013年充分暴露了出來,諸多行業產能過剩較為嚴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四萬億計劃”出臺,固定資產投資快速擴張,這些投資大多轉化成了企業生產設備,即產能。
當時的財政刺激主要集中在交通和電力行業,形成了大量的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加之房地產市場持續景氣,進一步刺激了鋼鐵、水泥、金屬等上游產業的快速復蘇和擴張。然而,近幾年我國經濟增速換擋,需求持續走低,產能過剩問題凸顯。
具體來說,我國產能過剩的行業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和傳統制造業,大致包括了:煤炭開采、黑色金屬開采、有色金屬開采、非金屬礦開采、造紙、石化煉焦、化工、化纖、黑色金屬冶煉、有色金屬冶煉、非金屬礦物制品等11個行業。其中又以黑色金屬冶煉(鋼鐵)、煤炭和有色金屬冶煉(電解鋁)行業最為明顯。
產能利用率之謎
為了探究具體行業的產能過剩情況,需要計算各個行業的產能利用率。然而,關于產能利用率的統計,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大多來自較小樣本的抽樣調查,且沒有具體行業的數據。雖然有學術研究利用計量方法對產能利用進行估算,但也存在一些關于準確性的爭議,各類研究得出的具體行業產能利用率有著較大的區別。
在此,我們以各行業的企業固定資產周轉率平均水平這一指標來近似替代產能利用率。之所以可用這一指標替代,是因為有如下近似關系式:

由于資產周轉率和產能利用率之間的天然聯系,我們便可將微觀企業層面的實際生產狀況與宏觀層面的產能利用問題結合起來,從微觀企業的運營角度去看產能過剩問題。
首先,從這兩個指標的比較來看(參見圖1),兩者之間的變化較為一致。

再來看產能過剩行業的固定資產周轉率變化趨勢(參見圖2)。2000年以來,相關行業的資產周轉率持續提高,直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開始下滑,但2009年后又開啟了持續約4年的升高,其背后是政府“四萬億”投資刺激。2013年以后,該指標又持續下滑,直到2015年下半年產能過剩問題爆發。

行政性去產能的來龍去脈
由于傳統制造業中大量國有企業的存在,行業調整產能的能力很弱,產生了大量的僵尸企業,加劇了產能過剩的影響,政府在此時便有必要開展行政性調整。
換句話說,在充分競爭的市場中,產能過剩可通過快速調整產能和企業退出來解決,但由于國有企業面臨的市場約束不足,市場出清過程緩慢,政府最后被迫介入其出清過程,這使得供給側改革成為市場出清過程的最后一環。
另外,央企尚且容易調控,地方國企卻不那么好調控——在GDP、就業和納稅指標的鉗制下,地方政府不斷補貼產能過剩企業,去產能效果受限。最終,這也促使了更具強制意味的行政性去產能命令下達到大量具體企業。
2005年-2016年,國務院及發改委不斷出臺調整產能的政策,其針對性和強制性越來越明顯(參見表1)。

去產能的總體效果
經過2年半的行政性去產能,工業的整體產能利用率得到了較好修復(參見圖3)。

不過,從美國等國家的經驗以及歷史數據上看,產能利用率在 80%以上算是合意水平,低于80%則存在一定情況的產能過剩。
2007年至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期間,美國產能利用率下降至 67%的歷史低點,在 2009年6月觸底回升,目前處于上升階段,但仍未恢復至歷史均值80%的水平。
整體上看,我國目前產能利用仍未達到80%,去產能進程仍在繼續。并且,2018年第一季度的去產能有所反復,依然面臨嚴峻挑戰,也反映了企業面對限產政策的反彈動機。
鋼鐵和煤炭的去產能效果
下面,我們來關注一下去產能的兩個“老大難”產業——鋼鐵和煤炭。
從一開始,這兩個產業一直是去產能的重點。關于鋼鐵行業,2016 年2月,國務院出臺《關于鋼鐵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意見》,明確表示用五年時間退出粗鋼產能1億-1.5億噸。對于煤炭行業,從2016年開始,用3至5年的時間,再退出產能5億噸左右、減量重組5億噸左右。
相比于鋼鐵和煤炭當前的產量規模,去化產能的任務并不繁重(鋼鐵5年預計總產量40億噸,煤炭為200億噸)。從近兩年的成效來看,這兩個產業去產能效果較好:鋼鐵化解了產能1.2億噸,煤炭化解了產能5.4億噸,均超出了預期。
事實上,這兩個產業的固定資產投資早在2014年便開始走入負增長通道(參見圖4),這為以后幾年的去產能工作打下了較好的基礎。

從當前效果來看,得益于前期固定資產投資調整得當,煤炭去產能的效果似乎更好一些,煤炭產業的利潤率爬升更明顯(參見圖5),但業界很多觀點認為,其去產能預計要延續至2020年之后。

從工業品價格走勢來看,去產能深刻地影響了宏觀經濟的上游市場。2015年底-2017年初,PPI指數直線提升,這一方面反映了去化產能的成效,也從側面道出了鋼鐵、煤炭等產業的企業盈利改善的原因。所以,至少從價格方面來看,工業產能與需求的匹配程度正處于修復中,市場出清速度在加快。
不過,值得強調的是,行政性的去產能壓制下獲得的價格上漲刺激了企業擴大產能的反彈動機。一旦政策趨于放松,產量便開始增加,由此帶來了價格下跌(參見圖6)。由此看來,行政性的去產能多少與經濟中自然的均衡狀態有所距離。

還有哪些產業過剩?
其他具體產業中,去產能情況各有不同,具體情況分析如下:
(1)電解鋁等有色行業得益于下游需求的快速增加,去產能基本完成,未來還需要進一步推進供給側改革控制總量,提高質量。
(2)基礎化工子行業去產能進程不一,化工類部分產品的產能利用率達到了80%,而PVC 和 PTA 行業產能利用率有待進一步提升,但供需也已經逐步改善,而燒堿和滌綸等產品去產能也基本完成。
(3)建材市場上,水泥和平板玻璃產量持續上升,價格也自2015年底穩步提升,直到進入2018年才有所反復,其去產能已經進入后期的穩步調整階段。
(4)在汽車和家電兩個行業中,汽車行業的產能問題主要集中在商用車方面,乘用車產能整體處在合理區間,但車企之間差別較大,但隨著產能逐漸得到控制與重卡需求回暖,汽車行業產能過剩問題得到緩解。
(5)家電行業產能升級道路起步較早,且彈性較高,因此家電行業的產能問題不值得過于擔憂。
因此,除了部分石油化工子行業以外,其他傳統意義上產能過剩行業的去產能效果尚佳。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進入2018年以后,諸多產業的產量反彈明顯,價格形成了波動中下降趨勢(參見圖7),因而投資者需要持續關注相關企業在政策放松情況下的產能反彈。

綜合上述分析,行政性限產已經持續了2年半,仍然有一些產業存在產能過剩現象。并且,大多數行業產能利用率也都未達到合意水平。同時部分產業和企業反彈動機增強。由此來看,后續經濟仍將受產能過剩問題及限產政策影響,相關行業的投資前景也將進一步分化。